|
|
顾铮:太完美的照片对我没有吸引力
- 时间:2013/10/27 23:36:14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文/本刊记者 胡凌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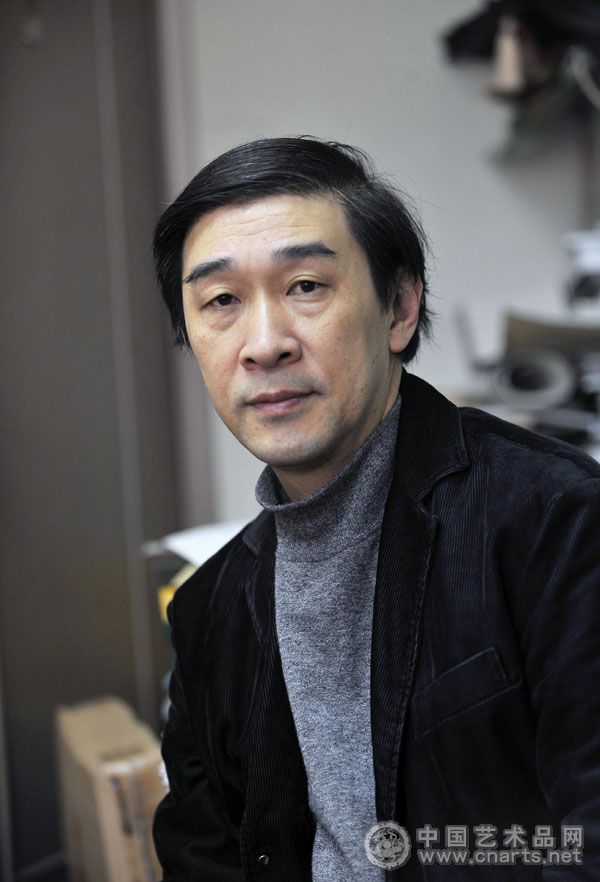 顾铮 戴焱淼摄影
与顾铮约了在番禺路上的一家咖啡店采访。刚从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亦称“荷赛”)回来不久的他,显得有些疲惫。很多人知道,顾铮是位犀利独到的摄影评论家,是颇具影响力的影展策展人,如今他又多了一个耀眼的身份:“荷赛”的终审评委,这也是迄今已举办了56届的“荷赛”终审评委团中出现的第一张中国面孔。
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顾铮出了名的严谨,说话有进有退,充满思辨,在课堂上针砭时弊的有感而发,也使他获封“愤中”(“愤青”的中年版)的雅号。相比较其他评论家绝少亲自操刀创作,顾铮却热衷于做一个拿着相机的城市“游手好闲”者,在他“欲说还休”的照片里,透着一种神秘与超现实。严谨与荒诞,使命感与游戏感,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让我一时有些迷糊,但我很快发现这种矛盾也体现了顾铮一贯的审美趣味:喜欢不确定,不喜欢被定义。
“荷赛”,不仅是评委在考照片,照片也在考评委
对于“荷赛”的邀约,顾铮坦言是有些出乎意料。去年8月,顾铮收到一名担任荷赛基金会监事(supervisor)的策展人邮件,主要内容是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荷赛邀请担任评委”,顾铮回复表示“愿意”,之后没有消息。“去年10月左右,我收到正式邀请邮件,才知道我要担任的是终审评委。”
世界鼎鼎有名的“荷赛”,为何会青睐顾铮呢?顾铮表示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然而看看他的履历,人们也能猜中七八分了。十多年来,顾铮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摄影这个话题,已出版十多部摄影与视觉文化研究著作,发表很多论文。顾铮还是一位知名影展策展人,2005年他策划的第一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1年,他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当代摄影艺术》一书,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多国文字,在很多国家的书店可以买到,也被一些顶级图书馆作为馆藏。顾铮还是有近60年历史的美国《光圈》(APERTURE)杂志的供稿编辑,是柏林的《欧洲摄影》(EUROPEAN PHOTOGRAPHY)的编委。在荷赛官网上,顾铮的身份介绍主要是大学教授和策展人,他确实是9位终审评委中唯一在职的高校教授。
2月8日至15日,每天差不多工作12个小时以上,顾铮坦言,很辛苦,完全没有时间游玩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是他收获了很多。
记者:今年“荷赛”评选出的年度照片并不是你最喜欢的,你更偏爱意大利摄影师阿莱西奥·罗门兹拍的《叙利亚之困》,为什么呢?
顾铮:从专业角度来讲,年度照片是一张无法挑剔的照片,从时机的把握,视角,信息量,强度,都非常优秀。但让我觉得稍稍有一些不满意的,是照片没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完美得像电影剧照,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包含不确定性的作品,获得一般新闻类组照一等奖的《叙利亚之困》中,有一张照片不是太实,模糊、昏暗,从摄影技巧来说可能会为人诟病,但我觉得这更符合21世纪战争、革命、冲突、动荡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生命、生活、命运的不确定性,而作者还通过照片的模糊、虚化加强了这种不确定,也展现了人类为追求更自由、美好的生活而甘愿付出的那种努力与牺牲。相对于这张照片,太完美的照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甚至还说过,荷赛的形象已经基本固定,如果选择这种照片也可以有所突破。
记者:第一次当“荷赛”评委,对你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顾铮:在评审照片的7天时间里,特别是评奖阶段,除了年度照片,我们一直是在点评、讨论中度过的,每个评委都必须从作品的专业特色等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我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不仅通过评审来了解当今新闻摄影的动态,也向一起工作的其他几位终审评委学习他们看照片的方法与观点,以及他们的敬业态度。大家都非常享受由于评委不同组合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上的惊异感。所以不仅是评委在考照片,照片也在考评委。
记者:在评审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顾铮: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评委中有一些人表现出的反思,犹豫——我的这种考虑会不会有问题?或者说,听了别人的意见以后,我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大家会有这样的反思精神,不会说太肯定的话,时刻保持有一种警惕心。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性别,并且认识到每个人的立场和视野都是有限制的。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精神,保持了充分倾听的姿态。所以我觉得评委会主席让每个评委都发表意见确实有其意义所在。
记者:“荷赛”是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一直被争议的是得奖作品总是与战争、暴力、杀戮、血腥有关。不过,在前两年荷赛的图录里,我们发现已经增加了“日常生活”、“当代议题”的分类,在你看来,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顾铮:我个人的体会是,荷赛不希望只停留在热点和突发的新闻上,而是希望摄影师更有问题意识地去关注日常生活的、更具普遍性的题材,这也是对大量的题材火爆的参赛作品的一种平衡。日常新闻奖项的出现,为参赛摄影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促使他们探寻平凡生活中不平凡之处。从近年来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荷赛允许新闻与纪实,甚至纪实与艺术之间跨界,这说明荷赛是有反思能力的国际大赛。
记者:你也当过国内一些摄影大赛的评委,国内的比赛与国外相比最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顾铮:国内的很多摄影大赛审美标准、美学趣味还是太低,较少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大量获奖作品离现实越来越远,那些风景摄影仅仅只是没有个体立场,更没有独到的现实关怀的景观再现。同时,还有一些摄影比赛配合各种商业活动。总体而言,现在大量的摄影比赛无法引导、提升现在的摄影水准,无法对当代文化作贡献,看上去表面繁荣,但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个性的比赛,比如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举办的三影堂艺术摄影奖,着重推新人,有特定宗旨,有一定的国际性。
记者:“荷赛”非常注重组图,但是在国内很多摄影大赛上,看到的都是单张获奖,对此,你怎么看?
顾铮:荷赛要求组照是12张,在评选过程中,摄影师的12张照片会在屏幕上一张张打出来,最后这12张还要在屏幕上缩成一个群组,评委们会看这些照片相互的关系、色调、影调,叙事上的展开:高潮、结尾,节奏等,进行整体的评判。国内摄影大赛单张得奖,偶然性相当大,不通过完整的系列的观察,很难对参赛者的摄影理念、对摄影语言的把握进行较准确的评价。
评论有它自身的目标与追求
顾铮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摄影评论家身份,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日本攻读博士时,他翻译撰写了大量介绍国外摄影历史和现状的文章。1999年学成归国后,顾铮着重关注当代摄影家的创作,把摄影作为当代的一个视觉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撰写了大量文章。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年轻摄影师是读着顾铮的摄影专著成长起来的,也以能被他“策展”为荣,因为经他策展的首届亚洲摄影双年展和首届广州摄影双年展,为整个摄影界的展出体系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
虽然在摄影界顾铮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但他依然常露忧虑之色,因为少有后来人。作为复旦新闻学院的教授、博导,顾铮集中于艺术理论、视觉传播、摄影文化史的研究方向,由于冷门,他每年接收的硕士生不超过5名,同时,还没有一个博士如期毕业,“开门大弟子”放弃学业踏入娱乐圈,“二弟子”为创业选择肄业;今年理应毕业的两名博士已申请延期。然而即便是跟随者寥寥,他还设置难关,直接封死直博这条路。顾铮解释道:“直博是一种看上去很省力,最后可能很不省力的做法。考博不仅能考察学生调动知识的能力,更能检验学生读博的决心与合适度。”
记者:评论时,你一般会倾向于怎样的角度、切入点?
顾铮:评论主要是以文本为主的,从历史现实的复杂脉络、创新的程度、语言等方面做出自己的判断,方式上可能存在两种不同:一种通过肯定作品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东西的同时,也在暗示其他人创作中所忽略的东西;另一种,当一无是处的作品却获得好评时,要痛加鞭笞,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提示作用:是否大家的认识上出现了问题。我认为评论要有一定的倾向性,当然把优点、不足比较平衡地列出来也可以,但评论的色彩不够鲜明。
记者:你既是知名摄影评论家,又是颇具影响力的影展策展人,但我听到一种说法,在国外评论家为避嫌一般是不太进行策展活动的。
顾铮:倒也不一定,我认为策展活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评论活动,是把当下一种摄影现象、某种趋势通过展览的方式加以呈现,最终展现的不仅仅是展览的过程,也体现了审美趣味。
记者:现在在文艺批评领域,评论家与艺术家的关系很微妙,那么在摄影界,这种关系如何呢?
顾铮:这涉及到舆论的生态问题,摄影家是否能积极面对建议性的评论。确实有些摄影家与批评家是南辕北辙的,有摄影家说,我根本不看评论家的东西,甚至说大量从事评论的人是傻瓜,搞了一辈子没有搞明白过,就是为了在大学里讨一口饭吃。从某种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艺术家一定要意识到,你的作品一旦呈现出来,就有着天然被评论的宿命。当然,还出现了一种比较差劲的,求你时卑躬屈膝,关注了他后,就翻脸不认人了,这样的行为明显是利用评论。
记者:在你看来,摄影评论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顾铮:作为摄影家积极地希望评论家、策展人了解他的工作,这是天经地义的。反过来,其实评论本身也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不只是为当下的实践服务,也需要不断通过评论的工作进行理论的升华。我觉得摄影家、评论家各有各的事情做。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搞”摄影评论与理论的人,以指导者的面孔出现,一本正经地给人家指点,君临摄影家头上,那很荒谬。
记者:业内认为,你与林路等撑起了中国摄影评论界的半壁江山,这是上海的骄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折射了评论界的沉寂、冷清。
顾铮:实际上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在摄影评论这个空间,从事这个领域需要不间断地耕耘,不问收获地耕耘,像我跟林路是作为人生的志业来做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投身这方面,当然也有生存方面的压力。目前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上,在摄影评论方面还是新兴的,估计最起码再需要50年时间才有比较确定的地位。
摄影是寄托内心隐私的视觉表露
采访间,顾铮会偶尔顺手拿起相机对着窗外的景物按下快门,随后他给我看拍的照片,原来是咖啡店门外铁栏上做装饰的黑色的铁皮狗,“躲”在淡黄色的桌子下面,整个画面在虚实相间中透着一种奇妙的小情趣。
我问他:“那么喜欢摄影,为何没有在摄影道路上继续下去而转向理论呢?”顾铮立马“纠正”道:“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摄影呀”,一脸的认真。我赶忙补充解释道,“我指的是职业摄影”,但我很快意识到摄影对于他而言,无所谓职业非职业,无论走到哪里,顾铮都会随身携带一个轻便小巧的数码机,他抗拒过于仪式化的创作姿态,喜欢随意抓拍。摄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顾铮回忆,起先是在家里拍摄家人,后来是在同学家里,互拍合影不过瘾了,索性把同学父亲“文革”前的肩章制服、大檐帽穿戴上,化了妆,拍摄设计情节的剧照,甚至为拍《红色娘子军》里面的角色,把自己绑起来吊起来等。中学毕业后,为了更方便把玩相机,顾铮干脆进了照相机厂工作,平时也经常在街头抓拍。
1980年代,为质疑当时摄影圈中流行的 “愉悦视网膜”的艺术,顾铮等人兴起了一个真正具有民间色彩的摄影群体“北河盟”,彰显了反叛的姿态:不甘于被不受质疑的美学观和摄影观所左右,敢于拿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尽管“北河盟”主创者的形象已经成为了某种传说,但顾铮依然延续了在影展上所提出的城市影像的概念,他称自己是个城市的“游手好闲者”(波德莱尔语),他意图“遭遇”一幅作品,而非功利性地去“擢取”城市的细节。由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厚体验以及新锐的艺术观念,这位悠闲的“游手好闲者”总能“随手擒来”一些好作品。细看他的照片,如同都市空间的悬疑剧,荒谬而又超现实。顾铮说,“荒诞”源自一次少年时候的惊吓。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次不经意的偷窥,他们在一辆停在街角的面包车里看到躺在车里的死者一张僵硬的脸,从那时起,顾铮就觉得这个城市中处处充满了出人意料,充满了荒诞和奇幻。虽然学生们觉得顾老师比较严肃,“把七情六欲都藏了起来”,但是照片却透露着他细腻的情感,“摄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观看、分享、发现,是寄托自己内心一种隐秘的东西的一种视觉表露。”
记者:为何没有往专业摄影方面走下去?
顾铮:我曾经也想做专业摄影师,1991年到日本留学时是想念摄影专业的,无奈学费昂贵,需要去打工才能支撑下去,我一直体弱,一看到需要体力劳动,马上就被吓住了,后来就选择在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类文化研究科读比较文化研究专业。现在回过头看,这方面的训练对研究摄影史、对摄影现象的评论都是很有帮助的,是很好的积累。而且我现在也一直在拍照。
记者:从国际视野看,你怎样评价国内摄影师现在的水平?
顾铮:如果把国内优秀的摄影师推到国际上毫不逊色,像上海的陆元敏,他的照片能给你一种惊喜,一个意外,很放松,问题是这样的摄影家太少,而且也没有太把他当宝贝。
记者:为何这方面的摄影师那么少?
顾铮:主要在于观念,摄影师的素养。也有一些摄影师对我说,顾老师,你关注关注我,我心里想,要死了,你一张照片得奖,你就认为自己是摄影家啊?我怎么通过你的一两张得奖照片知道你对摄影有没有持续兴趣,兴趣背后对世界有怎样特殊的看法。现在国内一些摄影师获奖无数,但没有自己的想法,跟着不同摄影比赛的不同主题,一会拍这个,一会拍那个,没有专业的定位,而且思维方式也比较单一,以为风光摄影就是起早贪黑拍到一抹朝霞,应该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被破坏的风光也是风光摄影的题材。
记者:当你是学者时,你的批评犀利直接,有一种全力提升摄影界的急迫感、使命感,为何当你拍照时,这种使命感似乎被抛开了,更多的是个人化的表达,充满了游戏感、荒诞感?
顾铮:这要看每个人对自己角色的认同。我不是个记者,也不必用记者的角度观察和叙事,我只是叙述自己眼中的城市。现在摄影越来越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手机等设备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其实挑战性更大,并不是人人用日常性那么强的东西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异常的。我更提倡人们因地制宜地用适合自己身份、现状的做法比较自然地拍照。摄影最好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并非一定要承担太多的使命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