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韩师“不教一日闲过”
- 时间:2014/3/31 10:44:38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文/唐吉慧
 五月的北京,柳絮飘满整个天空,缠着老树,缠着房子,缠着行人的头发,也缠得人过敏。朋友不停打着喷嚏,周末预备下去潘家园溜达溜达的心情,都随着一次次的喷嚏消散了。我跟朋友打趣,不如一起出去把柳絮收了起来,明年做一床“鸭绒被”吧,他笑笑说:“那我这喷嚏恐怕这辈子打不完了。你出去走走吧,别浪费了这么好的春光,我在旅馆里‘避敏’。”
一个人肆意游转在琉璃厂,看字看画看石头,忽然瞥见一家画廊对着正门的墙上挂着韩天衡老师写的书法横幅,四个字,篆书,写“乘物游怀”。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几个字了,特别有亲切感,如同老师站在面前一样。
我于2002年跟随老师学习书法篆刻,从此像着了魔似地喜欢上他的艺术,他的篆刻,他的书法,他的绘画,强烈的节奏,新奇的构图,画面往往半露半藏,虚虚实实,一派迷蒙。他的线条独具魅力,粗如屈铁,细若游丝,浓如乌云,淡若秋水,动如急风,静如皎月;粗而不俗,细而清健,浓而不腻,淡而凝香,动而不乱,静而文雅,让我时时获得审美的满足,精神的愉悦。
前几天友人聊起一则旧事,说1975年上海有次书法展览,评审方式特别,书协安排了一位老书家对一位中青年书家,书写同一内容,择优而展,类似现在的“同台PK”。韩先生恰与赵冷月先生同写一首毛主席诗词,结果评委觉得韩先生的草书作品好,淘汰了赵冷月先生的作品。韩先生得知此事,觉得相当不妥,立即去了赵冷月先生家里,跟老先生赔礼,谁知老先生反而劝他宽心,笑着说:“我看了你的作品了,得张旭《古诗四帖》三昧,以篆运草,气势恢宏,写得确实好。”关于张旭的《古诗四帖》,鉴定界曾有一番争论,谢稚柳鉴为真迹,徐邦达先生认为“狂獗怪异”,非张旭所作,并定为劣迹。七十年代末韩先生去北京,见到徐邦达先生便与他聊起《古诗四帖》:“论真伪,谢老与您各执一词,我的学问浅不够发表意见,但您说‘劣迹’,我觉得古代写狂草,至唐代,都不算真狂,到了张旭的《古诗四帖》才真见狂妄,真见狂情,使篆书逆笔法180度四周运动,前无古人,对草书而言是种伟大的创造,您何以说他是‘劣迹’呢?”邦达先生听了大为意外,思索一会儿后欣然接受了这位后生的意见,虽然这不改变邦达先生对《古诗四帖》真迹存疑的看法,却再不提它是劣迹了。没有对草书如此深刻的理解,我相信韩先生一定写不出让赵冷月先生称赞的草书,也一定没有底气和徐邦达先生争论。
韩先生七十年代有三年时间少涉书印,而专攻绘画。那时期以临摹宋元名家,诸如顾定之、梅道人、柯九思、赵孟頫的兰竹为主。资料匮乏的年月,他借来画谱拍成照片,而后临摹,每天工作之余临摹五六个小时,遇周日、过年过节,师母为他留下几斤光面打发一日三餐,便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就从早上六点可以用功到半夜两点。学习画画半年多,有次在杭州,时值9月依然暑热难挡,先生随身带着一柄折扇,有艺友问他借来看扇上的画,但见几杆墨竹素心凌云,只是没有落款。艺友反复观赏扇面,问竹子是谁画的?先生回答:“我画的,画了半年多,你看如何?”艺友的眼神顿生惊讶,望着韩先生没有掩饰自己的赞叹之情:“真是你画的?如果真是你学了半年多才画的,你将来一定是个大画家!”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韩先生艺友的话早已应验,韩先生于印家、书家之外的的确确成了一位大画家。他说书画印就像一个个马蜂窝的蜂壁,如果打通,便能贯通。在他那么多绘画的题材中,朋友们最喜欢他金色的荷花。水佩霓裳,翠叶吹凉,一朵朵荷花迎着微风在他洒脱的笔下舒卷开合、嫣然摇动,染红池塘,香遍池塘。几只鸟儿倚荷寻幽,争唱采莲小曲,还有谁不愿意缓楫轻舟去向花间住?画荷花,大块泼墨、大块泼彩的还有张大千,还有谢稚柳,张大千与谢稚柳是挚友,韩天衡是谢稚柳的学生,他们的荷花各成风景,各有意境:金线勾勒的荷花盛开在他们的画里,也将绽放在中国画的长河里,千年不败。 “
八十年代《新民晚报》发表过老师一篇文章,《不教一日闲过》,可惜我一直没有寻到,不过大致意思能够想象,人生苦短,不能让一天白白的过去。当年85岁高龄的齐白石每日作画,有天风雨交加,于是心绪不宁,坐卧不安,未画一张画。待第二天雨过天晴,老人家精神大振,顾不上早餐在画室挥起毫来,数张画毕,他在最后一张画上落款题道:“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不教一日闲过,催人奋进,靠的是内心意志的坚持。文革期间,韩先生有回在干校敲猪圈,平时毕竟不做重体力活,八磅重的大榔头半天下来,中午吃饭手抖得拿不住筷子,只能将一双筷子合在一起捏在手里,往嘴里扒饭。吃过饭他坚持刻印,刀握在手里仍然抖,他自忖:你不是要做篆刻家吗?手抖,饭能吃,印为什么不能刻?就这样刀歪歪斜斜在石头上起起落落,最终印刻得不理想,但无疑是内心意志坚持的一次磨炼了。
老师性子比较急,有回约了午后3点在他家碰面,2:45分的时候我进了他们家小区,心想这回不会迟到了,偏偏这时候他打来电话问怎么还没到,弄得我心里憋出几滴汗。师母也常劝他凡事慢着些,可他偏偏慢不下来。尽管如此,他在艺术上却是慢火熬制的一锅浓汤。他告诫学生,艺术是一辈子的事情,境界的高深和风格的独立是学问的积累和胆识的提炼,做百乐斋的弟子便要沉下心五年十年,临帖临印,步步为营,而他也是如此实践着。他自省,对待艺术要有正确的态度,不盲目骄傲,将自己立足历史,与历史上的名家比,比差距,比缺点,比出自己的尊严来。他有自己的精神,好比林风眠的“皮蛋鸟”、唐云的“公安麻雀”,韩先生三角形的鸟,正是他人文精神的表达,这只“韩鸟”不放弃,不言败,不退缩,不满足,不断思考,不断追求,不断探索,因为他觉得搞艺术总是固守陈式,那有什么意思?不好玩了!是这样一种精神,让他屹立艺坛常青。近年他的篆刻“老学生”、“如何是好”、“劣迹斑斑”等印,不正是他进取的心迹吗?古人说:“青春留不住,白发自然生”,感慨生命的青春过去的时候,不禁要为老师艺术青春的依然而欢呼——艺术能让人拥有第二个青春,真好。
琉璃厂回来,朋友的过敏稍有好转,我却像过了敏似的,心思一直留在琉璃厂那幅老师的书法上,它就像满天柳絮做的“鸭绒被”盖在了身上,这辈子我怕是逃不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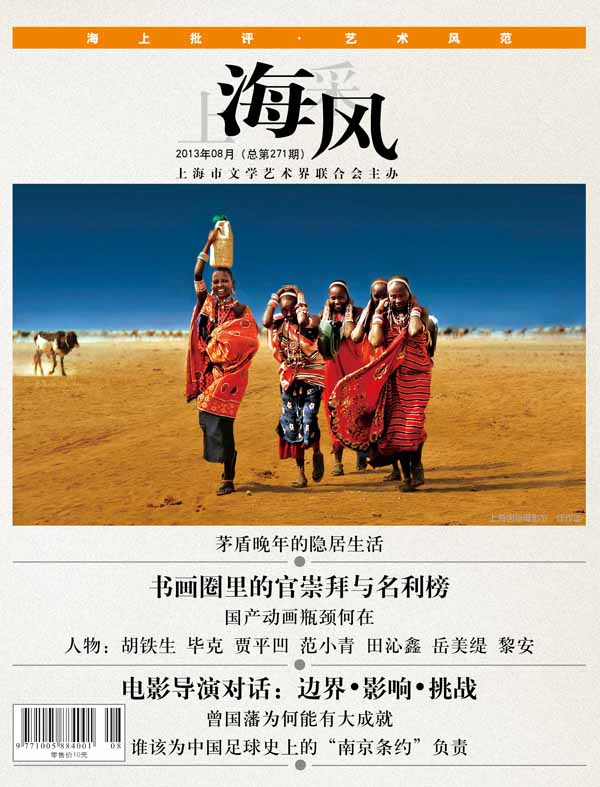

心接八荒

翠岭流云

映日吐芳
|











